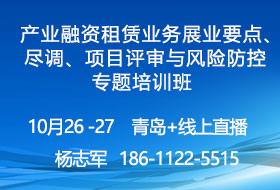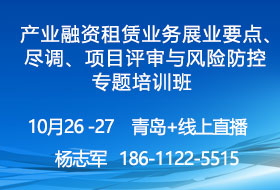以租賃業的跨越式發展促實體經濟轉型
中國租賃業的發展獲得了國家層面的力挺,其深層次意義不僅在于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于如何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問題,更從戰略層面著眼于中國經濟未來的持續健康成長所需要的內生性動力營造。
中國經濟的下一個增長奇跡能否出現,既取決于經濟再平衡的實現、前瞻性技術的投入以及產業與金融資本出海和人力資本的提升,更取決于經濟戰略轉型能夠如期實現,而在此過程中,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業不僅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更有難得的行為空間。
對長期處于大金融領域后來者的融資租賃業而言,國務院日前連發的《關于加快融資租賃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及《關于促進金融租賃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兩個重要文件,標志著中國租賃業的發展獲得了國家層面的力挺,其深層次意義不僅在于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于如何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問題,更從戰略層面著眼于中國經濟未來的持續健康成長所需要的內生性動力營造。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么
眾所周知,金融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不僅是撬動資源優化配置,促進價格發現的最重要中介,亦是產業發展與制度變遷的基礎性支撐力量。就增長動力而言,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在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說是政府主導下的投資與出口,但現在看來,即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本身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從資源稟賦和市場空間來看,盡管中國的人口、勞動力資源、市場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間,但卻很難自動孕育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國內有學者主倡的“后發優勢”其實也只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可能條件。
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究竟是什么呢?我們不妨看看一個有趣的現象:被譽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并未成為經濟高速成長的主要推手,倒是實體經濟部門在問題叢生的金融體系下實現了高速增長和發展。這是一個值得所有研究中國經濟的人深入考究的問題。有學者提出,究竟是這種被體制轉型所扭曲的金融體系支撐了中國經濟的虛假繁榮?還是中國實體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是從轉型時期金融體系的種種漏洞里“鉆”出來的?
其實,從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構成要素來看,得益于政府對民營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得到了顯著優化,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終于被激發出來,民營經濟因此獲得了快速發展。加上FDI的推動,以及在民營、外資企業的效率輻射和競爭下,國有企業本身經營效率的不斷增進,共同構成了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繁榮的動力機制,不僅要致力于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以及技術的不斷升級,更要建立一種能夠使經濟保持活力的增長機制,從而保證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得到持續有效的激發,以避免經濟出現非制度性衰退。
需要尋找內生動力
但從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長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增長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從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來說,中國迄今為止暫未找到能夠全面支撐政府與市場所期待的下一個經濟奇跡所需的關鍵性動力之源。過去凱恩斯主義色彩濃厚的宏觀經濟政策引致的資源配置扭曲、資產價格泡沫、產能過剩以及收入差距擴大等負效應的發酵,直到今天依然還在痛苦的消化中。各級各地政府由于在保增長上投入了太多的資源,但這些資源的經濟績效并不顯著。另一方面,關鍵領域改革的滯后乃至被人為拖延,又在相當大程度上加大了經濟轉型的成本,使得政府面對的經濟發展沉疴越積越重。從這個層面來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承擔著兩個重要使命:一是全面清理這些年來經濟改革積下的諸多沉疴,二是在清理經濟發展沉疴的同時,通過啟動新一輪的戰略性改革,為下一個經濟發展周期提供政策和動力準備。
因此,在熟知中國經濟發展路徑依賴和出路的李克強總理看來:投資之于中國經濟增長最多只有工具價值。事實上,經濟學意義上也沒有所謂的“消費驅動型增長”概念,至于進出口,其實是經濟體之間資源稟賦的一種互換。所謂“投資” “消費” “出口”三駕馬車,至多只是經濟增長的手段。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持續有效增長,本質上并不取決于投資或出口驅動,而取決于知識、信息、研發創新等所引致的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中國必須加大對研發與人力資本的投資,盡快實現要素價格市場化,提高勞動生產率。
其實,當前中國根本不缺激活經濟有效增長的元素,正如中央多次強調的,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重要紅利是通過改革來釋放,而改革紅利的釋放絕不是簡單的簡政放權,而是市場活力的有效發掘。例如,改革進展緩慢的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必須加速推進,而備受期待的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亦離不開市場準入門檻的實質性降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構建,任何單一改革措施的推出,哪怕設計得再完美,恐怕也很難真正發揮作用。進一步,對中小企業以及小微企業的貸款支持,亟須多層次的金融機構的有效支持。筆者最近通過實地調研發現,無論是沿海地區還是廣大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在獲取貸款過程中也遭到廣泛的歧視。而要解決這些老大難問題,必須在政策體系上、執行層面上有剛性且具操作性的文件與配套機制出臺,并有強有力的保障機制。
從這個角度而言,國家有關發展租賃業的文件出臺,可謂正逢其時。
融資租賃業實質地位偏低
相對于美國等金融發達國家而言,我國融資租賃業起步較晚。1981年,中信投資的中國租賃有限公司和首家中外合資的東方租賃有限公司先后開業,標志著我國融資租賃業開始起步。此后,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緩慢,直到2009年,中國融資租賃交易規模也僅為410億美元,市場滲透率只有3.1%,與美國(17%),德國(13.9%)等發達國家相差甚遠。不過,在 2006至2010的5年間,中國融資租賃業呈幾何基數式增長,業務總量由2006年約80億元增至2010年約7000億元,增長了86倍。2009年全國在冊運營的融資租賃公司約117家,融資租賃合同余額約為3700億元。2010年全國在冊運營的融資租賃公司約181家,融資租賃合同余額約為7000億元。而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融資租賃總部企業已達到3185家,比上年底增加了983家;行業實繳注冊資金達到10030億元,比上年底增加3419億元;全國融資租賃合同余額達到36550億元,比上年底增加4550億元。
不過,整體而言,中國融資租賃業在中國整個社會融資棋局中的實質地位依然偏低,其不到4%的滲透率與商業銀行動輒70%以上的滲透率相比,差距十分明顯。盡管租賃資產已廣泛分布于航空、航運、電力、機械、醫療、印刷等領域,有效地擴大了相關行業的投資、生產和消費,在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帶動了租賃行業的快速發展。但作為金融工具的重要組成部分,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依然較弱。
另一方面,就融資租賃業本身面臨的發展約束而言,由于長期以來融資租賃公司對資金來源的數量和成本較為敏感,不能吸收社會存款,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同業拆借、銀行借款等批發型融資,穩定性較差,抵御系統性風險的能力較弱。需要合理平衡盈利性和流動性的關系,控制流動性風險,加強資產負債的組合管理。雖然最近幾年融資租賃業發展迅速,但差異化發展并不明顯,同質競爭現象明顯。
發展空間廣闊
中國經濟的下一個增長奇跡能否出現,既取決于經濟再平衡的實現、前瞻性技術的投入以及產業與金融資本出海和人力資本的提升,更取決于經濟戰略轉型能夠如期實現,而在此過程中,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業不僅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更有難得的行為空間。
正如國務院兩個文件所指出的,加快發展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是帶動產業升級的重要舉措。例如,對船舶、醫療器械械、飛機等行業的融資租賃企業,在相關企業設立子公司時不設最低注冊資本限制,在經營資質認定上同等對待租賃方式購入和自行購買的設備。這對相關企業的發展可謂雪中送炭。而對高端核心裝備進口、清潔能源領域租賃業務的支持,更是促進產業升級的及時之舉。尤為關鍵的是,文件特別提出要支持融資租賃公司與互聯網融合發展,加強與銀行、保險、信托、基金等金融機構合作,創新商業模式。探索融資租賃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融資模式相結合。相信在后續的落實過程中,或大大激活民間資金進入政府主導搭建的公共產品體系的熱情。
至于《關于促進金融租賃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所強調的要突出金融租賃特色,增強公司核心競爭力,發揮產融協作優勢,支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引導各類社會資本進入金融租賃行業,支持民間資本發起設立風險自擔的金融租賃公司,擴大服務覆蓋面。可謂綱舉目張。十分清晰地給出了發展金融租賃業的路線圖。眾所周知,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亟須良好的政策環境支持。例如清晰的產業規制,有效的監管、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環境。尤其是透明和有效的契約法及執法體系、良好的會計制度與慣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當然,還需要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國內外資源配置力的金融企業,以及能夠全方位參與全球金融分工,領軍國內資本市場發展的戰略性金融人才隊伍。
中國在穩步做大租賃業產業規模以更好促進實體經濟轉型的同時,更應著力重視培育一大批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的產業控制力型租賃企業,盡快形成基于領先技術并整合金融服務和品牌運營的綜合性競爭優勢,這應是中國發展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業的目標指引。
來源:企業觀察報
上一篇:偉祿收購前海美林融資租賃
下一篇:中國融資租賃三十人論壇成立租賃資產交易專業委員會